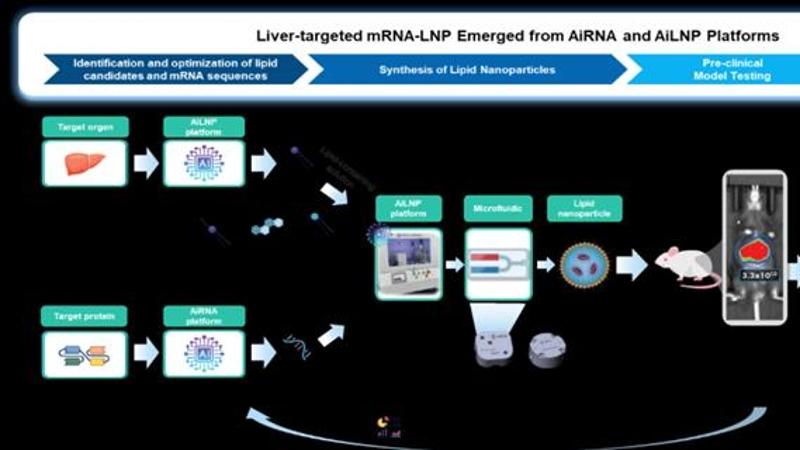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報記者 張蓋倫 崔爽 策劃 劉恕 李坤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周五。和每個周五一樣,可以上學、上班。但送別楊振寧先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王東峰牽著孩子的手,站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外的隊伍里。他們隨著長長的人流緩緩移動。小男孩手里捧著一束白花,卡片上寫著“楊爺爺,我們永遠懷念您”,落款是孩子的名字。
10月24日上午9時,天氣陰沉,北京氣溫很低。八寶山革命公墓外,車流人流不息,接送人員的大巴車沿著馬路延伸,一眼望不到頭。

公墓的幾個大門前都排起長龍,人們身著素衣,手拿印有訃告的白紙,遠遠望去像一條條漂著白花的黑色河流。
他們來到這里,做這件唯一的事——送別。
當天上午,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10月18日,這位“純粹的科學家、堅定的愛國者”在北京逝世,走完103歲的科學人生。
之后,在他傾力創辦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在他出生的地方安徽合肥四古巷,在他工作過33年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在他任教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學……人們送上花束,留下卡片,以各種方式寄托追思。
楊振寧或許是他們的親友、師長、同業。但于更多自發送別的人而言,楊振寧是與他們素無交集的人。
這也應和了2021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詞中的那句話:“您貢獻給世界的,如此深奧,懂的人不多;您奉獻給祖國的,如此純真,我們都明白。”
“我在送別一顆星,也在走自己的路”
楊振寧去世后,他傾注心血創立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清華高研院”)專門開放了緬懷室,接受各界友好人士吊唁。
很快,清華高研院一層的長廊就擺滿了鮮花。


其中有三束,來自住在上海的黃譽程。他今年28歲,楊振寧是他神交已久的“人生導師”。
第一束花,是10月19日讓外賣員送的。花順利送到了,但他仍覺得不夠。
“一個對我這么重要的人離開了,如果不去現場,我會后悔。”黃譽程21日一大早動身前往北京,因為沒能預約上清華大學入校,他22日才真正走進清華高研院。
黃譽程又買了兩束花。一束代朋友送,一束為自己送。他在卡片上寫道:“感謝您在這個世界留下的一切,您的智慧一直在照耀和引領著我。愿您一路走好,精神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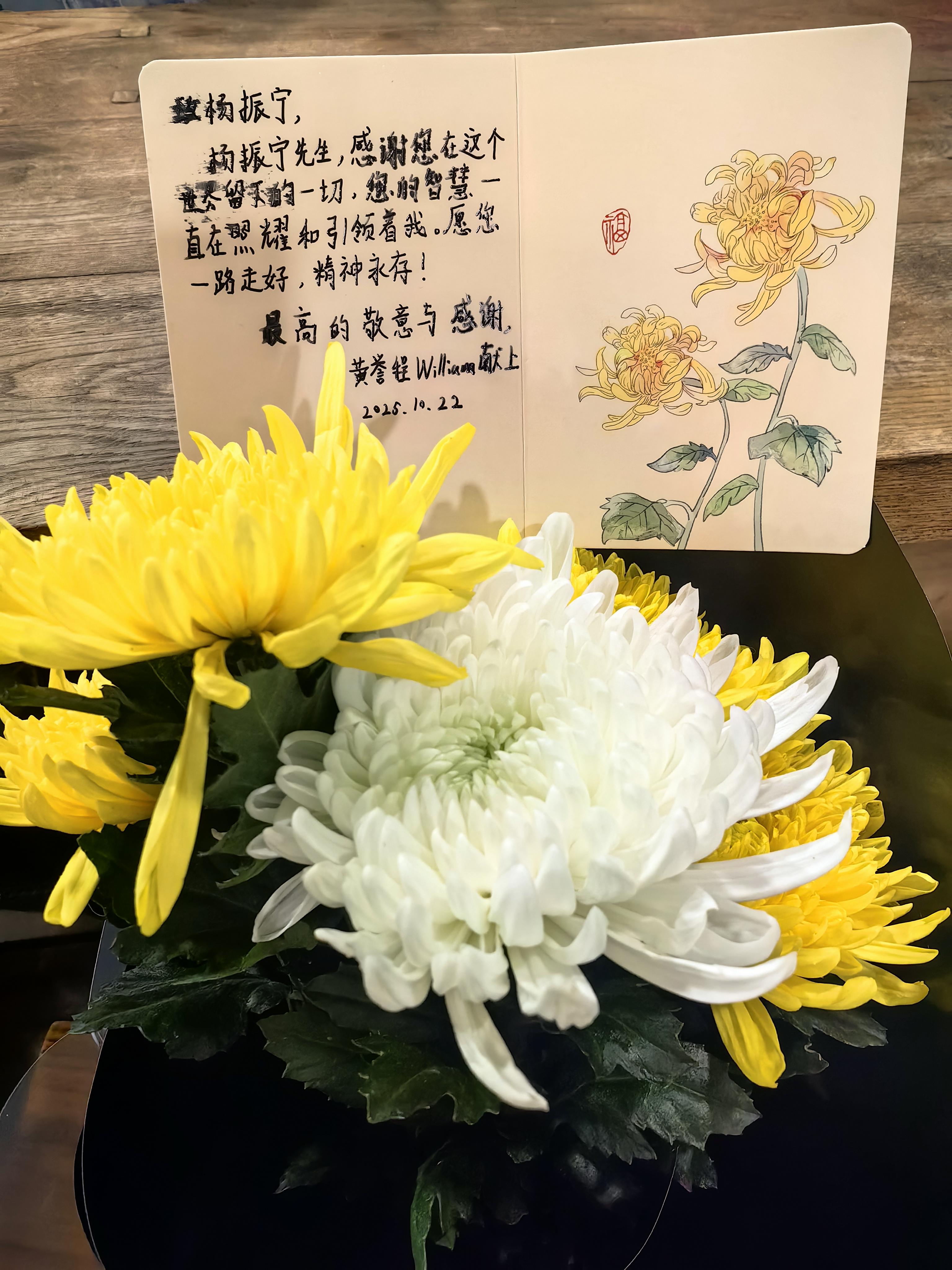
楊振寧對他有特殊意義。說來奇怪,但確實如此——很多個迷茫得無法入睡的夜晚,他靠著看楊振寧的采訪、講座和視頻來汲取力量。
黃譽程一度不知道人生該如何度過,不知道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課題是什么。一次,他刷到了一則楊振寧的視頻。視頻里,楊振寧講道,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品味)。
“我覺得,這話說得太有道理了。”他開始看更多的視頻、采訪,走近這位百歲老人的智慧人生。
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楊振寧說,每個人有天生的對于某些東西的偏愛,對偏愛加以培養是很重要的。如何看待生命?楊振寧說,個人在整個宇宙當中是非常渺小的,但并不代表他就不必或者是不應該去想辦法做出來他能做的事情……
近一年來,楊振寧是那個在黑夜里為自己點燈的人。得知楊振寧去世時,黃譽程覺得很懵、很無助。“就像一棵大樹突然倒掉了,我心里空了一塊。”
從緬懷室出來后,黃譽程走得很慢。“我在送別人類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的星星,我也在走自己的路。”他這樣形容當時的感受。
宋奕霖從更遠的地方來——新加坡。
他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念碩士,研究方向是微電子器件設計。
得知楊振寧去世時,宋奕霖正在吃午飯。“當時就沒什么胃口了,拿筷子的手都有些顫抖。”他曾經有一個愿望,想親眼見到楊振寧。“現在這個愿望再也實現不了了。”
宋奕霖崇拜天才。初中剛學物理時,老師就跟他們講,楊振寧和李政道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上了高中后,宋奕霖開始嘗試了解兩人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又聽說了楊振寧與米爾斯提出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這可是與麥克斯韋方程和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礎物理理論之一,我更崇拜他了。”
中國人也可以將名字寫入世界科學史史冊。正如楊振寧所說,他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宋奕霖坦言,小時候比較天真,想成為像楊振寧那樣的人。后來他意識到,想達到楊振寧這樣的成就,談何容易。
最終沒有繼續學物理,但宋奕霖還是選擇了和物理相關的微電子專業。“楊振寧先生算是我最開始的那個引路人。”
看到清華大學開放緬懷室的消息后,宋奕霖臨時決定去一趟北京。10月21日中午,他從學校出發,先到吉隆坡中轉,凌晨到達北京,在大興機場待了一晚上。22日一大早,他去往清華大學,為心中的天才獻上花束。
“能送先生一程,已經心滿意足。”宋奕霖說。
“還是想學成歸來,報效祖國”
清華大學電機系研究生黃舒曼帶著幾位大一新生來到緬懷室。
每年清華大學新生入學,都會集體觀看原創話劇《馬蘭花開》。它講的是“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的故事,劇中也多次提到鄧稼先的好友楊振寧。
黃舒曼輕聲地說:“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每個看過《馬蘭花開》的人,都會被兩位科學家的家國情懷觸動,他們以各自的方式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是鄧稼先給楊振寧信中的一句話。
50年后,在自己百歲時,楊振寧講起這句詩。他說:“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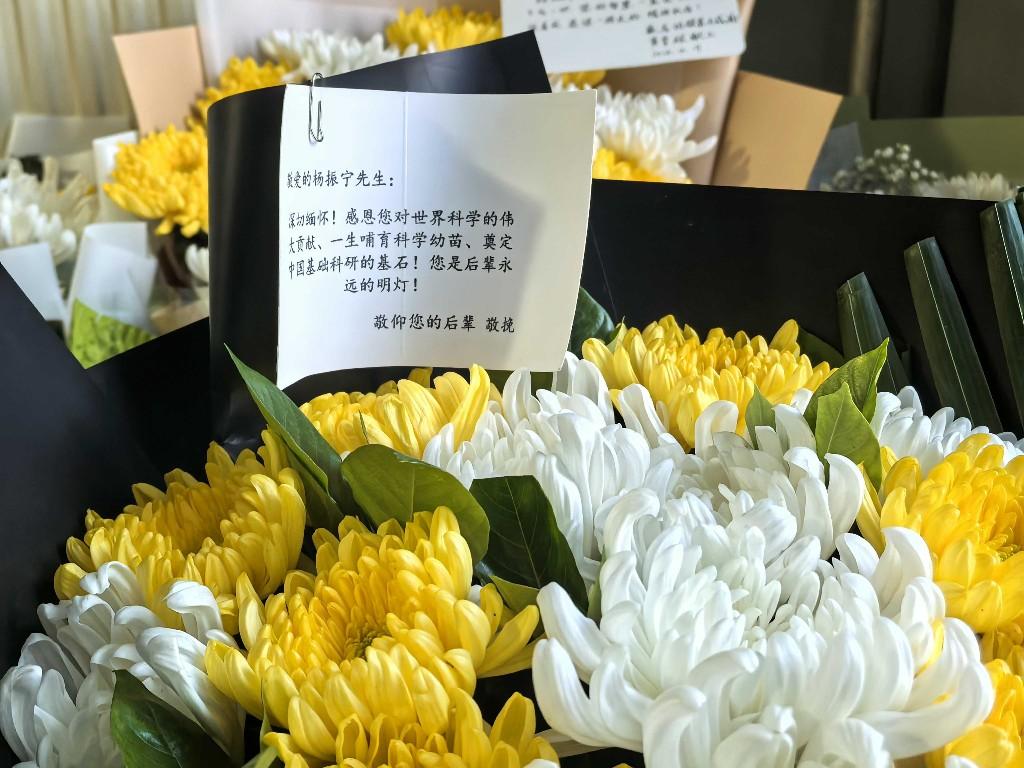
楊振寧將自己的人生比作一個圓,從清華園啟程,波瀾壯闊大半生,又回歸故土。2003年,81歲的楊振寧由紐約石溪遷回北京清華園定居。他將住所取名為“歸根居”,在詩中寫道:“神州新天換,故園使命重。學子凌云志,我當指路松”。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所說,物理學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一半是他的家國情懷。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新中國訪問,掀起大批華裔學者訪華熱潮,被視為架設中美學術交流橋梁第一人。1996年,為協助清華大學創建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為清華高研院),楊振寧捐出積蓄房產,行走多方募集資金,積極參與人才選聘、經費籌集、發展規劃等各個環節。
在他的邀請和帶動下,許多優秀的世界級科學家陸續加盟,推動清華高研院在理論凝聚態物理、理論計算機、天體物理、密碼學等領域形成一批重要成果。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說,楊振寧是“定海神針”,幫助清華大學引進了“一批原本不可能回來的大師”。
“他的回歸,對國家和清華的貢獻是無法計算的。”緬懷室外,一位清華大學80多歲的老教授動情地說。
天色將晚時,“清華家屬”賴薇莉趕來了。她的丈夫王龍幾年前從美國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
王龍曾在美國IBM研究院任高級研究員,科研方向是可信計算和分布式系統。2021年,他得到回國工作的機會。當時,夫妻倆已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回國意味著房產、事業、交際圈,統統拋棄。
但賴薇莉沒有二話。“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有中國根。在國外,好像不管做出多少成績,都是在給別人打工。還是想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她的眼中淚光閃動,“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受到像楊振寧先生這樣老一輩科學家精神的感召。所以,楊先生走了,我們要來送一送。”

“給他們種下一顆小小的種子”
賴薇莉其實來了兩次,每次都是帶著孩子來。
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看起來還懵懵懂懂,拿著介紹楊振寧生平的冊子走出緬懷室。大一點兒的哥哥前一天已經來過一次,他在門口等待媽媽和弟弟。哥哥大聲說:“我當然知道楊振寧,我們科學課上學過。”
但他或許不知道,這位課本上的科學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父母的人生選擇。
孩子們還小,不懂悼念是什么意思,但賴薇莉希望給他們種下一顆小小的種子。“也許過了很多年后,他們會回想起這樣一件事,曾經吊唁過一個偉大的人。”
和賴薇莉一樣,王東峰也想在孩子心里種下一顆種子。
他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10月24日一早,王東峰帶著孩子從位于五道口的家趕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告別儀式。
他以孩子的名義買了花,還在幾天前送了孩子一本楊振寧的傳記,小朋友已經讀了幾十頁。
站在送別隊伍里,他回憶起2009年的一段往事。
當時他剛來北京,還是一名學生。看到“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去世的消息后,和很多普通人一樣,他自發去了設在北京航天大院的靈堂。“錢老的家就在航天大院一棟不起眼的二層小樓。他去世后,一樓被改成了靈堂,接受公眾吊唁。”王東峰回憶,在那棟小樓的一樓,他進門獻花鞠躬,瞻仰了錢學森的遺容,和錢老的家人握了手,說了保重。
此刻,時空重疊了。他牽著正在讀三年級兒子的手,送別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和他一樣帶著孩子參加吊唁的普通人不在少數。王東峰說,這些自發的送別,體現了一種對科學家的敬重、對愛國者的敬重,也是一種對精神傳承的期許。
楊振寧曾說,科學的發展,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不僅需要科學家的努力,也要有大眾的支持,它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楊先生是現世成就最高的華人科學家了吧?”10月24日,八寶山外送別的隊伍里,不知是誰喊了一嗓子。
“是啊,再沒有了!”有人答。
“會有的!正有小朋友在為此努力。”王東峰輕聲接了句,笑著看向兒子和他手中的花。
記者手記丨給大時代留一張小切片
張蓋倫 崔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吊唁者告訴我們,她曾猶豫是否要到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清華高研院”)獻花——一個普通人,好像沒有資格送別楊振寧這樣一位科學巨匠。“但是我還是來了,正因為是普通人,才更應該來。我們或許不懂高深的物理理論,卻無時無刻不在享受科學進步帶來的福祉。”
問她身份時,她只留下了自己的網名“吉光Gigi”,理由是“我就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吉光Gigi覺得,楊振寧的故事與精神,能通過普通人的視角被記錄和傳遞,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之一。
這也正是我們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我們好奇,人們為什么不辭辛苦,從五湖四海甚至海外遠道而來,送別一位從事艱深基礎物理研究的科學家?
清華高研院的工作人員說,每天有約3000人次來悼念楊振寧。我們隨機攔下一些人,撞見了許多質樸的情感。
一位75歲的老人說,他在北京“打工”,干些修訂地方志之類的文化工作。他感謝清華高研院開放了這樣一間緬懷室,讓普通人有機會表達一份敬仰之心。
附近醫院的醫生董雪花來了兩次清華大學。第一次沒預約,她沒能入校;第二天約上了,她立刻又來。說起楊振寧,她熱淚盈眶。我們看到,她后來一直在高研院附近徘徊,直到夜幕降臨。
中國報業協會集報分會的兩位會員背著大包來了,他們帶上了9份10月19日刊登楊振寧去世相關報道的報紙。他們說,楊先生雖然離去了,但他已經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輕人。
還有吉林長春從事航空相關工作的“青青草”女士、廣東佛山做了三十多年生意的龍先生、貴州遵義來北京旅游的祖孫三人……
采訪前我們也曾擔心,與楊振寧先生沒有直接交集的普通人,能說出什么新故事?但接觸他們后我們意識到,打動人心的,就是那份藏在大家心里的“真”。
我們常說要“弘揚科學家精神”,要營造“尊重人才、尊重科學”的良好氛圍,這些宏大的命題,最終都要落到人的具體行動里。
送別楊振寧,就是這樣一次集中抒發、集體行動,我們記錄著一個大時代的小切片。在這位影響力跨越世紀、代際、圈層的科學家身后,是國人對那些為國家作出過貢獻的人的樸素敬意,是對一段科學報國歷史的駐足回望,也是人與人之間感情的真實涌動。
吉光Gigi說,偉大的科學家從來不是神壇上的人物,他們是照亮人類文明前行的燈塔,我們每個受惠于這種光芒的人,都有責任銘記并傳承這種精神。




 網友評論
網友評論